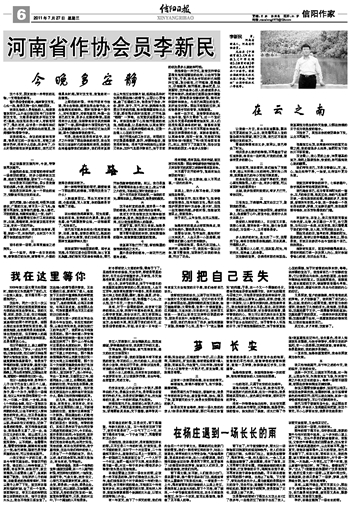2009年第二场大雪不约而至时,我的伯父永远离开了我们。又一位亲人离去,我不得不再一次提到死亡。
这些年,死亡一次又一次以不同的方式或近或远或明或暗地与我的生活发生着关系。我的大哥、姐姐、奶奶、三叔、伯父相继离去,每次面对死亡的现实,生与死遥遥相对的两个茫茫世界,却那么接近地在我面前来回交错。虽然我知道,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谁也无法抗拒,但目睹亲人的离开,关于生命的脆弱无奈和悲哀,总是笼罩在心头。
伯父平躺在床上,脸上凝固着微笑,像是进入了梦乡,一点也不可怕。父亲告诉我,伯父当时正和他围着炉火愉快地说话,谈到张家结媳黄家盖房吴家得子,都是关于幸福的话题,说着说着,感觉大脑发晕,接着口齿不清,头歪靠在了椅靠上,再也没有醒来。过程如此简单,短暂的一瞬却是伯父的一生。
伯父一生勤俭辛劳,养育四个儿子(长子已去世),结三个儿媳,得六个孙子。娶一房儿媳,盖一处房子,得一个孙子,都要办一场酒席,伯父从未向亲朋邻居借过一升米、一口碗、一双筷、一分钱。在他七十年的生命里,伯父一直都在为好日子劳作着,这种自强自主勤俭持家的作风,让他不曾有过人情和债务的背负。所以,这正是他离去的方式,了无牵挂,干干净净,体面从容。我坐在伯父的旁边,记住了他最后的表情。我不相信他的离去,我想他是太累了。这一生,他办过太多的大事,却从顾不上休息,以至几十年来每天他都凌晨起来劳作,从不间断。他需要休息,需要安安静静、踏踏实实地睡上一觉。他已看到,眼前已是芳香四溢的生活,可以安然地离开。
小我父亲近十岁的三叔,是在今年春天离去的。春暖花开的时候,杨庄的山山岭岭都披上了新绿,布谷声声,油菜花开,紫云英满田。三叔要结儿媳了,他重新盖起了新房,为张罗好儿子的婚事,在做最后的房间清理时,不慎从凳子上摔了下来,就这样在喜庆来临的时刻,去了另一个世界。我回到村庄,看见三叔的犁耙还静立在明亮的水田,刨子正嵌在木头上,我也不相信三叔去世了。这些细小的情节提示着我,正在忙碌的三叔,家里来了客人,他就放下正在赶牛整理秧田的犁耙或正在制作家具的刨子,陪客人说话去了。他的院落里,公鸡正在嬉戏,母鸡正在觅食,生活那么生动,可房前屋后再也不见三叔进进出出的身影。
还有大我一岁的兄长育生也是在今年去世的。秋收忙完的时候,从杨庄传来消息,在新加坡打工的育生死了,我同样也不相信这是真的。那个身材瘦小声音响亮耳朵略背的和我一起长大的育生就这样死了?那个从小带头掏村庄最高处鸟窝的伙伴,那个听不清老师讲课回答不出问题经常挨打不愿上学的学生,那个满身油渍满脸污垢从老家为我扛来一袋大米爬上五楼的哥哥,那个为五十元钱遭无赖欺负给我打电话求援的兄弟,那个家有父母妻儿的男人,就这样走了。自小学毕业,育生一直奔波,正值而立之年,却客死他乡。山坡上,白雪皑皑,隆起的新的坟茔,育生安息在那里。我长时间停留在他的坟前,想对我的兄弟说些什么或听他对我说些什么,最终只能听到呼啸的风声。
近几年,杨庄先后有十多人离去,有男有女,有老有幼,有长有晚。村庄周围的山坡上,不断增加新的坟茔,就像村庄里盖起了一片新房。那些离去的人们毗邻而居,顺应四季,可曾想到活着的我们的哀伤?我在想,活着的我们,其实只是存在于生与死交替之间虚无的境地之中。今日的生,或许是明日的死;今世的死,或许是来世的生。生命如此脆弱无奈,我们无法主宰生死。当死亡来临,无法逃避,实在也无须害怕。我宁愿相信,这些与我们相伴的亲人,只是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很久以后,他们还会回来。轮回大致如此,有先有后,节序如流。
雪纷纷扬扬,真是一个洁净的世界!感谢这场雪,在一个人离开的时候,有这样浩大的映衬,一如来世,赤裸干净,气象大美。送走伯父,心情已不如回家时沉重。佛说,一念觉,即是佛;一念迷,即是众生。就像爱过,所以慈悲;正如懂得,所以宽容。凡俗的我们来世的一刻,就意味着要离开,只是,我的村庄中,下一个离去的人不知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