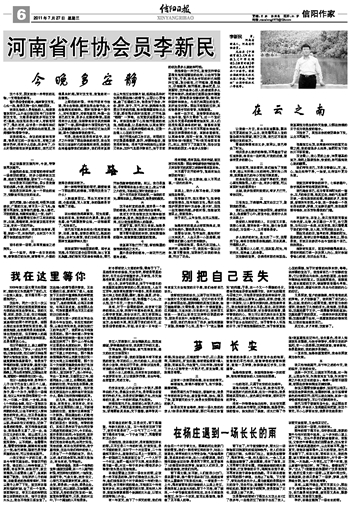我回杨庄的时候,正是伏天。雨下得频繁,年龄大的老人说,五十年没有这样下雨了,老天爷真是烂了,一口气下了二十天,把雨下得没有节制,一下子全下完了,再需要雨时怎么办?
仔细想想,我在杨庄时,没有遇到这样长的雨。只不过是二十年的时间,对我来说,是个不短的数目,但对于一个村庄而言,二十年确实不算什么。就像我们从早上一觉醒来,只是一眨眼的工夫黑夜就过去了。一个人对于一个村庄,如同一滴水对于大海,实在是渺小得不值一提。村庄一辈子有多长?要经历多少事情?我永远也无法知道。
在杨庄要碰上这样一场长长的雨,应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孩子们都会这么想。五十年,他们谁想在这个村子里住五十年呢?我小的时候,分不清时间的概念,不知道五十年究竟有多长,所以希望哪天的大雨,真能把人冲走,我就抱着家里那个洗脚的大木盆,让雨水把我带到山外去。
有一年夏天,连下了十四天的雨,我们相约去另一个村子看大水,那里的河比我家门前的要宽。我们一群没看过海的孩子,站在山坡高处,看浑浊的大水带走杂物,气势汹涌奔腾,莫名其妙的兴奋。在小小的罪恶里,我们满怀期盼地议论着:要是再下两天,就更像海了!幼稚而向往的声音,如被大人们听见,定会抄起铁锨,把我们拍死。
雨下得太稠,扯不断,人们就很少出门,呆在屋子里,搬个凳子呆坐在门边,痴痴地看雨水从屋檐流下来形成水线,一看就是一个上午。偶有披雨布肩扛铁锨的人从路上走过,是到田畈上检查水沟的。雨下个不停,淹了稻田,一个季节歉收或没有收成,在冬日里就很难熬过,作为一个农民,就无比得羞愧,像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
雨下长了,村子就安静许多,雨水让一切事物回归到原来的规则和秩序。老人们依在门框边打盹,头靠在门板上,就轻易地睡着了,偶有声响,一惊,流几滴口水,一会儿又点头瞌脑地睡着了。猪在圈里,没有了猪草,主人不再管它是否长膘,把洗碗洗锅的剩水倒在槽里,打发着猪的日子。鸡鸭关在笼子里,不再有在院子里争食的热闹。平日里在傍晚爱叫骂的那个婶娘,也停止了吆喝,下大雨了,看来她没丢失什么。最为寂寞的是那些半大的孩子,无处可去,就像蚊子样缠着大人哼哼叽叽的,哪家有孩子的哭声,定是惹恼了父母,屁股上挨了巴掌。
这是哪年的雨呢?下得这么大这么长?过了很多年,一些经历过了的孩子也成了老人,在雨天谈起雨,又会相互记忆。
应该还有一场雨,与我有关。
那年的雨下得不长,但非常凶猛。我家的黄牛与邻村的黄牛抵角,从十多米的山崖上掉了下来。这头牛是我们的全部家当,我敢说,父亲把牛看得比我们还要金贵。这头昔日在村子里威风凛凛的牛,从此英雄不再。整个夏天,我都在割草喂牛。正大的雨夜,我已早早地睡下了,实在太困,雨实在太大,我的房屋,被大雨淋倒,我被掩埋其中。村子里一声巨响,一片热闹,一片慌乱。过了两个时辰,我从废墟中被刨出时,转了转头,傻傻地问了声:“怎么了?我睡觉的房屋呢?”这是我到目前,经历过最大的一场雨。从瓦砾中爬出来,在黑夜里,仿佛只是做了一场梦,梦里,生死界线分明,如今,我依然活着。
其实,从离开杨庄,雨天不算太少。那些日子,每回都会如一场梦。直到现在,我仍认为,自己像是活在梦里,虚无而又具体,飘渺而又真实,无奈而又憧憬。
幸好,在杨庄遇到了一场长长的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