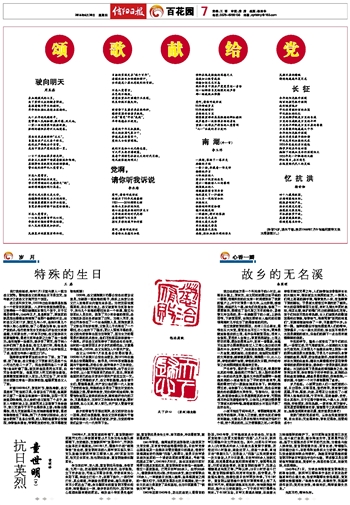朱家明
我出生的地方是一个叫沟角子的小村庄,坐落在丘陵上,面向东,当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的一霎那,喷薄四射的红光第一时间便映在了我家的窗户上。村子对面是一条大冲,从北往南,缓缓而降,绵延好几十里。祖先们依照地势,修建了一层层梯田,那便成了世代取之不尽的粮仓,紧傍着大冲边沿的,是一条蜿蜒而下的小溪。上游浅而窄,下游宽而深,当到达即将注入淮河的石婆堰湾湖时几乎成为了波涌浪卷的河流。
经过我家前面的那段,约有二三公里长,最窄处五六米宽,最宽处也不过二十来米。两岸是随地势起伏的土埂,各种杂草随意而生,没有人去修剪,更没有人去培土。春夏远远望去,土埂上野花烂漫,混杂在绿草丛中,别有一番景象,丝毫不比城市公园里那些经过人工精心造出的花海逊色半分。秋季来了,站在高处俯瞰,两边的稻田一片金黄,随风摇动,此起彼伏,宛如阳光照耀下的大海波浪。稻香随风飘来,满满吸一口,沁人心脾。曾经的挥汗如雨,曾经的风吹日晒,种种的辛苦之状刹那间遗忘得烟消云散。
严冬季节,最好是一场大雪过后,清晨听着北风的呼啸,陡然间打开房门,映入眼帘的是浑然一体的白色世界,整条大冲连同如腰带一般缠绕其间的小溪全都失去了平时的井然有序,厚厚的雪把它们一股脑地拥压在身下。瞬间的惊愕过后,当你静下心来细细地聆听,远处似有隐隐约约的潺潺流水声传来,节奏均匀,极为清脆。你起初会误以为是凛冽寒风的余音,可那连绵不绝似无疲倦的音节,让你马上判断出那是雪下面溪水的呤吟唱。酷寒寂寞的乡村因此平添了些许生机。
小溪不知成于何年何月,看那随弯就弯、深浅无序的模样,不像人工挖凿,或许先民们曾经有所疏浚,大概也只是在能架水车的地方临时打个坝,挖个深点的坑,以方便灌溉之用。小时候我曾经目睹过天旱之年,人们抬着如龙骨模样长长的木制水车,架在溪边水稍深的地方,一群男人们爬上高高的脚手架,唱着黄色小曲,使劲蹬着下面的踏板,于是溪水便经过车厢流进了稻田。车水的场面滑稽而又壮观,有时几架水车同时启动,相互比赛,粗犷的嗓门吼出的腔调杂乱无章。孩子们站在不远处看热闹,女人们被黄色的歌谣逗得绯红着脸,喘着粗气,嘴里骂着“该死的活鬼们”,双脚却像被粘住了一样,不愿挪开半步。乡野一隅,越荤的歌似乎越能提起男人们的精神,顶着暴日,一头一脸水汪汪的,谁也说不清是汗水还是溅起的溪水,但他们的脚下一点也没有减慢蹬踏的速度。
丰收的季节,整条小溪变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一场雨过后,天气晴朗起来,小溪里的水大部分已经无存,只有那几个如缀在丝带上明珠一样的深池里还是水波荡漾,于是几个伙伴结队拿着自制的鱼网、鸡罩,赶去捉鱼摸虾。能够网住的是浮在水面的白鱼条;蹲在水里慢慢用手紧贴着滑溜溜的淤泥往前摸去,逮住的一定是欢蹦乱跳的鲫鱼;水边的杂草下是黑鱼的理想藏身之处,倘若岸边有洞,你壮着胆子把手伸进去,抓到的必是鲇鱼或者鳝鱼。鲤鱼是最狡猾的,很难捉到。一番折腾,午饭时一个村子里都飘满了鱼香。
岁月悠悠。小溪两边的人们一如沉默的小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繁衍传承,享受着它的恩赐。平和、厚道、内敛、互帮互让也就成了小溪两岸人性格的主调。千百年来,虽然偏僻、贫穷,但乡风淳朴,日子过得宁静祥和。十里八乡,田陌相连,非亲即友,往来热闹,一家有难,四方援手。虽无显宦硕儒载诸史册,谦谦君子之风却源远流长。如果世间真有桃花源,或许就是这里吧!
我家门前的无名溪呵,从你生来就默默无语,自由自在;天地厚待你,春秋记得你,还要何名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