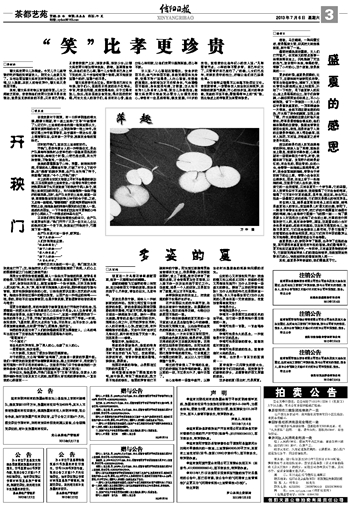□曾庆棠
在我老家村子南面,有一口四季明澈的清水塘。顺塘口南望,有一座土地庙(“文革”中被毁掉了)。记忆中,土地庙的庙舍约摸一畦菜地那么大,里面有道砖砌的台子,上面供奉着一尊土神爷。依稀记得土神爷慈眉善目,右手握有一柄龙头杖,膝上横摆着五谷,似有保一方平安、施黎民食粮的意味吧。
旧时的开秧门,就在这土地庙前进行。
开秧门,是往年家乡人的一种特殊仪式,是生产队里每年插秧时必定举行的一场隆重而热烈的农事活动。每每这个时候,山野已经泛绿,田水开始变暖,万物竞秀,一派生机。
淡淡的雾霭飘荡于山岭、茅屋、树梢和田野间,早醒的鸟儿啁啾地叫着,打破了村子上下的宁静。在“嗵嗵”的脚步声里,生产队长吹响了哨子,亮起嗓门喊道:“今个儿开秧门啰!”
村上的男女农民大都穿上平时不舍得穿的新衣裳,三五成群地往土地庙走去。一些青壮年劳力纷纷把秧圃田里于头天夜晚拔下的秧把子码入担子,挑到土地庙这边的田埂上,均匀地抛撒到一块块平整好的梯田里。这时,生产队长走进土地庙,燃起一柱香,恭恭敬敬地安放在供奉土神爷的台子前。之后,又点响一挂鞭炮。“噼噼啪啪”的脆响声即刻冲向田野的上空,细细袅袅的硝烟与飘来的白云融入一起,然后冉冉而去,一下子给我们这些尚不更事的少年娃子心间注入了一种莫名的神圣与庄严。
正在我们慌忙着捡拾鞭炮头的当口,生产队长高声地叫道:“秧门开开!”只见一位大伙儿公认的秧把式第一个走下田,快速地打开秧把子,弓腰插下第一棵秧。
生产队长高兴地一扬手,朗声说:
“插下头棵秧——”
人们齐刷刷地应道:
“秋后稻满仓;”
“插下二棵秧——”
“家人都安康;”
“插下三棵秧——”
“六畜也兴旺。”
伴着行云流水般的一呼一应,秧门就这么欢欢然地打开了。这,恰如把农人们一年的憧憬栽插进了田间,人们心上的那扇希望之门也随之姗然开启!
男男女女便很快卷起裤腿,踏入一块块水平如镜的田里,按着各自的性情、习惯和技术能力搭配到一起,自然地、默默地展开了插秧竞赛。
此时,你若站在田埂上,随意地瞧着一个快手插秧,只听见秧苗落入泥水的“叭、叭、叭”声,根本看不到插秧人的手动。那种律动的节奏与音韵,或许能轻轻拨动你的心弦,让你欣然赏识庄稼人技艺的炉火纯青,陶然分享劳动过程中的畅达快意,从而产生一种相应的和鸣——哦,是的,劳动不仅创造着美丽,也展示着风雅,更彰显着劳动者的高尚与尊贵!
而更为有趣的是,有的年轻男子趁着直起身打开秧把子的机会,迅即撩起一把泥水向另一块田里自己心仪的女子甩去。女人立身看看,没弄清挑战者是谁,也就不管他“三七二十一”,抓起一把稀泥即扔往下一块田的男子身上。于是,开秧门的热闹场面便这样拉开了序幕。一时间,你来我往,飞星流雨,泥巴水点四处飞扬。不论男女,也不分老少,全都尽情放肆地嬉闹。此所谓“开秧门,泥满身,接好运”。
和煦的春风因为有了人们的欢畅闹笑而更加温暖宜人,山鸟的鸣叫也因为有了这番热烈气氛的感染而显得格外动听。
“哥哥插禾!”
“个个插禾!”
布谷鸟的叫声传来,醉了男人的心,也甜了女人的心。
一层层梯田,渐次变绿。
一片片新绿,又连成了层次分明的巨幅画毯。
村子的那边,大公鸡“喔喔”地鸣晌了,炊烟自一家家的茅屋升起。我们一群野欢的孩童便开始朝着家里跑去。遇上这样的时日,没进家门就可嗅到一种平日没有的香味儿。这就是开秧门日子能够尝到的一次美味佳肴(其实也仅是烀块腊肉或烧碗河鱼、豆腐之类)啦!
流年似水,物换星移。开秧门虽基本于“文革”时退去,但家乡人的那种稻作传统习俗及其文化风韵,连同那久留舌间的醇香美味,一直在我的心际萦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