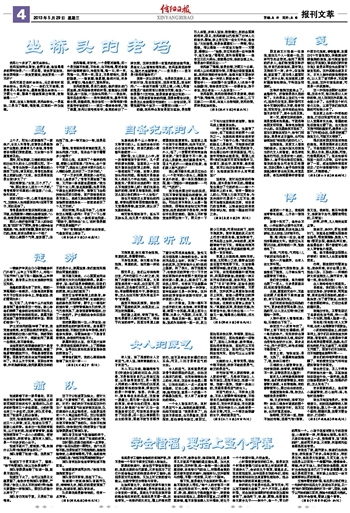朋友崔文川想做一批信笺,就找几个人一起做一批,这样可节约点费用。他问了周围的好多人,他们都觉得这事好玩,有自己的信笺纸,跟市面上见到的不一样,多牛。但说到做,就犹豫了,因为没人愿意写信了,有什么事,电话或网上即时通信都能解决,干吗还去写信呢。
这事好像到这就终止了。鱼雁传书,好像都是很久远的事了。大约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流行交笔友,那时候可不像今天聊QQ那么方便,经常写信,写来写去,在学校的生活也差不多写尽了,至今也没见面。
有一天,翻看这样的信件,真是觉得有沧桑感。干脆没事给朋友写写信,取消电话联络什么的。但这显然很不现实了,因为大家都在用这个,你专门写信去,真是有点古董味,也可能被笑话成“活在现代的古代人”。
说到信笺,民国文人喜欢玩的极多。比如木版水印信笺为历代文人所喜爱,鲁迅曾收集自行刊印,这是讲究一点的,周作人、俞平伯也都印过信笺,喜欢的信笺也可拿来互相赠送,这在《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里时常也能见到。有意思的是,鲁迅和郑振铎非常喜爱中国古代笺纸,曾经整理、发掘出《十竹斋笺谱》,并根据当时搜集到的信笺,委托荣宝斋印制《北平笺谱》,著名的《萝轩变古笺》就是在两位先生影响下被发现的。这种风潮也波及日本,日本人制作的信笺精美绝伦,让人见了爱不释手,不忍着笔。当然,这种对信笺的爱,可真是一种风雅事。
这一种玩法在那时也算时髦。这在今天,都只能是让人向往的事,找人玩玩这种风雅,机会就少多了。也许是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以至于我们连玩风雅的可能都少有了。
现在网上也有一种简单的信笺,打印出来就可使用,但总让人觉得有失水准,普通的纸张印信笺太硬了些,也大致找不到书写的感觉吧。倒是有人办起了《书简》杂志,但是否挖掘了信笺文化,可就不大清楚了。
偶尔还有朋友写信用传统的信笺,真是觉得有名士风范了。不免想起旧式文人的生活来,那么古典,那么风雅。可惜,已经雪泥鸿爪了。现在能够怀想起一些旧人旧事,似乎也神游了一回,忽地想到李清照有词云:“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摘自《萧山日报》朱晓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