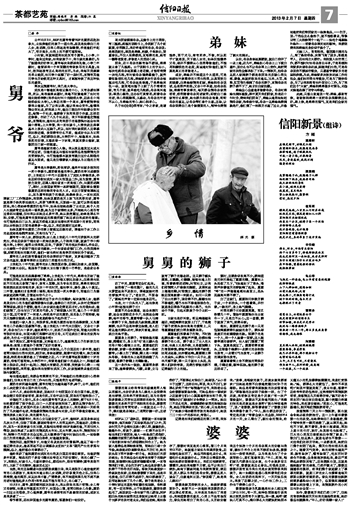□晏 华
去年10月2日,88岁的舅爷带着78岁的舅奶远赴加拿大,去投奔他们的孩子一道生活。虽说是投靠自己的儿女、是团聚,但我心里还是有些酸楚,毕竟他们年纪大了,背井离乡,生活上的不便可想而知。
小时候,我就知道我在武汉有个舅爷。上小学、中学时,他来过我家。在我家孩子中,我书读的算最好。为了鼓励我好好学习,舅爷每次来都送我礼物,小学二年级时,他曾送我一个双面翻的带吸铁石的文具盒。当时,信阳还没有这么高档的东西。为此,我每天美滋滋的早去晚回,在同学中炫耀了好一段时间。直到有其他同学也开始使用这种文具时,才逐渐冲淡了我这种快乐的感觉。
再次见到舅爷时,我已是大学生。
武汉是中部地区高校云集的中心,又有亲戚在那里,所以,高考填报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当时的湖北财经学院(我毕业时叫中南财经大学,后改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入学后的第一个周末,舅爷便到学校接我去他家。为了让我认路,他让我坐公交车。他领我到公交站点,把我送上车,他自己骑自行车跟着公交车走。每到一个站点,他都停下来向我招手示意,这样走走停停,行进了八九个站点后,我下车跟着他走到他家。直到现在,他在站点向我招手的场景偶尔还会在我脑中浮现。上大学前,我一直在读书,人情世故这类事基本上没进入过脑子。所以,当时我对麻烦别人这事感觉比较迟顿,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他或许也认为正常吧,总之,我们都很自然。大学四年中,每逢周末,如果没别的安排,又想改善一下伙食,我就直接去他家,就像回自己家一样随意。
舅爷是他家的核心人物。我从没见他发过火或大声说过话,但他的意见与想法在家里总是能得到充分的贯彻执行。也可能他根本就没有提出过什么明确的意见与要求,他只是引领着家人按他认为正确的方向行进。
舅爷是大学教师。听长辈讲,他早年在家乡信阳的一所中学教书。舅奶曾是他的学生。舅奶的学习成绩很好,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考上了武汉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即分配在武汉一家大型国企工作。因为爱情,舅爷努力发奋,后调入湖北省直一所高校工作,与舅奶团聚了。那时,正值国家两弹一星研制期间,国防事业需要像舅奶这样的物理专业的人才。北京方面曾商调她过去。因为舅爷和孩子的缘故,她最终没去,一直在武汉那家工厂工作到退休。我觉得,如果说舅奶是天上放飞的风筝的话,舅爷就是那手拴风筝拉线的人。风筝飞得再高,只要线一拉,就可以轻松地收回来。我心里始终替舅奶打抱不平,如果当初她选择了去北京,她个人的人生旅途肯定会是另一番风景。她为这个家牺牲太多。不知她内心是否有过委屈与遗憾,但在我认识她这么多年里,她从没流露过,始终是那么平和、安静。可能是舅爷的爱和家庭的温暖消解了她追求自我成功的渴望;也可能是她自己认为,家庭天经地义就应当排在所有选项中的首位。而我则从女性独立方面考虑得多一些。总之,我们没探讨过此事。
如果说舅爷在舅奶工作的事上曾拖过后腿的话,那他在子女工作上的态度却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了。
舅爷有一双儿女,都很优秀:女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同济医科大的研究生,毕业后供职于湖北省一所知名医院。儿子和我同级,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上学时,他常去找我玩,后来,干脆娶了我的校友作媳妇。毕业后,小夫妻俩一个供职于湖北省的媒体、一个在省政府部门工作,生活美满幸福。即便用现在的眼光看,他们一家也绝对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家庭。
舅爷的儿女们没有像他们的母亲那样安于现状,更多地则继承了其父亲的基因,像舅爷那样去追求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舅爷的女儿到美国进修,后移民加拿大,改国籍,成了加拿大公民。现服务于加拿大卫生部下属的一个单位,是政府公务员。
可能是姐姐的选择影响了弟弟。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弟弟也开始了他的移民历程。先是举家移民香港,然后从香港又移民加拿大。但弟弟与姐姐不同的是只拿到了绿卡,没有入国籍。因为专业的原因,弟弟的移民历程显然比姐姐艰难的多,长达十年的时间,他在学习、磨合、融入中渡过。三年前,他媳妇才念完博士课程,现在美国一所大学教书,而他自己为解决家庭团聚问题,目前还在奋斗之中。
舅爷是坚强的,他从没阻拦过子女外出的脚步,每次谈到儿女,他都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骄傲与自豪。他靠自己的打拼,从农村走到城市再到省城。按这个逻辑,他的儿女应该比他走得更远才对。也的确如此,他们做到了,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了缩短融入时间,他儿子十年没回过中国。这可害苦了一双老人:特别是年迈的舅奶,因思念儿子而抑郁,每天只能靠安眠药入睡,后来竟连药物也不起作用了……
在他们一家人身上,我很矛盾。我既为舅奶当初的选择惋惜,又为舅爷的儿子选择出国感到不值。他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出国时,父亲七十多岁,母亲也已六十多岁。他姐弟两人中,姐姐已在国外定居,而他夫妇俩也有很好的职业,在国内既可照顾年迈的父母,又可追求自己事业的优秀与成功,为什么一定要远走异国他乡呢?
知子莫如父。舅爷能理解、支持他的儿子。他解释其儿子打拼努力的结果是:客观上使他孙子受到了更好的教育。
舅爷身上表现出的那种坚韧让我敬佩。儿子出国后的十多年里,他们老两口独自生活在武汉。刚开始,身体还硬朗,随着年纪的增大,体力逐渐衰退。特别是在舅奶患上了抑郁症之后,八十岁的舅爷还要照顾七十岁的舅奶,艰难可想而知。大学四年中,我曾是他们家中的成员之一,和他们感情上很亲近。我们一起爬山、到武大赏樱花、打网球、交流读书心得……相处得很愉悦。我常想,假如我当初留在武汉工作,应该能减轻点他们的孤独与寂寞吧。
每当想起他们,我都会有深深的不安,不知他们生活得怎样?心里牵挂他们,但我又有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只能是常打电话问候。
舅奶的状况越来越糟,舅爷的精力也越来越不济。终于,去年,他们的女儿决定接父母去国外共同生活。
去年八月,表姑和我通话,说她9月中旬回国办父母出国手续。走前,她会陪父母回老家看看,算是告别。父母年迈出国,回来的可能性很小了。
计划赶不上变化。思乡心切的舅爷等不及女儿的陪伴,便于8月中旬,在给舅奶留了张字条后,自己一人回老家信阳来了。舅奶见到字条时,已联系不上他。忙给国外的女儿和我打电话。他的女儿、我的表姑一天给我打了几次越洋电话,我能感觉到她的焦虑与无奈,只好不停地安慰她,直到我联系上她父亲、我的舅爷为止。
当我见到舅爷时,我的心立马就安定了。去年,他88岁,虽说身体动过几次大手术,但除了耳聋、糖尿病等老年人的常见病外,其他还好,走路也行。因为一直保持读书的习惯,思维相当清晰!88岁高龄的他,不用任何人帮助,独自完成了从家打的到武昌火车站、买火车票、坐火车、到信阳站下车、转乘中巴车回乡的全过程。这大概得益于他平时独自生活、一切依靠自己打理的缘故。我心中暗自称奇,对他越发敬佩。
到信阳后,他回到乡下,在他父母及姐姐的坟前祭拜。他见了每一个他记得的亲友。他甚至还不忘去调解亲友们在“文革”期间产生的矛盾与隔阂。总之,他把想办的事都办了。
他给我讲了他和舅奶在武汉的生活及出国后的善后事宜。当他讲到多年积累、精选的四千多册书籍无法带走又不好安置时,我的心颤了一下。我明白,对读书人,书意味着什么,漂泊在外,语言有障碍(舅爷英语不行),又缺了书的陪伴,他该怎么过?
当然,我的这些顾虑与担忧都没表露出来,我只是很开心地劝他把所有的心思都放下,高高兴兴地去和儿女团聚,好好享受天伦之乐。但我心里清楚,他的阅历、识见比我丰富、广博得多,我不知道我那几句不咸不淡的话对他能起多大作用?我有点虽不能为而为之,尽心罢了。
10月5日,舅爷、舅奶顺利抵达加拿大。我从传来的照片看到:女儿带父母游玩,在渥太华湛蓝的天空下,在国会山前,老两口和女儿合影。舅奶一扫过去的倦容,开心地笑着,舅爷的表情有丝不易察觉的忧郁。或许又是我多虑了……
春节将至,远在异国他乡的舅爷舅奶,祝愿你们一切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