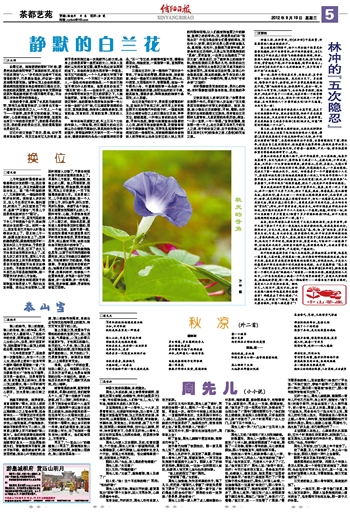□王大明
白露过后,淅淅沥沥的雨时下时停,硬是把炎热的信阳带进了凉爽的秋天。前些日子还在西关“八一”步行街东边楼宇下叽叽喳喳的燕子,已是燕去巢空,好似被一夜秋风刮得无影无踪。望着头顶上空空的燕窝,猛然间想起摆放在单位楼前的三棵白兰花,昨夜的疾风骤雨,该不会像去年秋天那样被狂风吹得盆破枝断吧?顾不得吃早饭,不由得三步并作两步赶到单位。
在我的骨子里,塞满了长风烈马般的狂野,面相又生得蛮荒粗犷,让谁看也不像一个柔情若水的养花之人,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搭界。或许是父亲的缘故,不知从何时,心底里却滋生了喜花的情愫,说起来也有三十年的养花资历了。养的最早的是白兰花,养的最多的是白兰花,养的最得意的也是白兰花。
记忆中的父亲除了养花、吸烟,似乎再没有其他嗜好。没见过他有过几次笑容,甚至于没有听到过他一次爽朗开心的大笑。他身上仿佛是压着一座沉重的大山,活在人世间时从来没有直过腰,魂灵永远尘封在深深的地下。在他的身边我永远有着一种窒息、喘不过气的感觉。一个十几岁随大军南下留在信阳的青年、一个不到三十岁风华正茂的人、一场政治浩劫的牺牲品、一个连自己都说不清为什么的理由,他莫名其妙地成了“黑五类”的一员——右派分子,从此父亲就步步维艰苟活在这个巨大的阴影之下,人越来越沉默,言语少得如一无所有的乞丐。从我记事时,他的影像永远定格在抽着一毛七分钱一盒的“公字”烟,伫立凝视着院里的白兰花,直到患肺癌,饱受身心摧残后辞世。无言的他、无言的花、无言的世界、无言的人生。
每年在梅花凋谢之后,叫上三五个力壮的年轻人,一阵吆喝,把三棵硕大的白兰花树从办公楼前厅里抬出。春风渐渐吹落去年的衰叶,春雨滋润着片片新叶一天一个样地生长,镶嵌在新枝内朵朵小尖椒模样的花骨朵,“五一”节过后,伴随着枝繁叶茂,慢慢由绿而白,相继绽放,一茬接着一茬,直到深秋方才作罢。
三棵白兰花中,有一棵相伴了我20多个春秋,干粗似我的臂膀,绿荫如盖,树姿挺拔,恰似一棵参天大树的微缩盆景。两头尖、中间宽、大而厚的叶子,青翠碧绿,宛如一叶叶绿色小舟,叶腋里掩映着一朵朵娇小玲珑、清秀雅致的花蕾。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随风摇曳,婆娑多姿、阵阵淡淡的幽香扑鼻而来,沁人肺腑。
白兰花竞开的日子,是我最为惬意的时光,犹如农夫于秋收之时。每天早上走进单位那不大却停满汽车的院子时,一眼就能瞅见办公楼前台阶之上的三棵白兰花树,亭亭玉立,郁郁葱葱,一种难以言状的生机与旺盛,平和与热烈,静默与淡雅就会由眼睛进入心田。新枝不停地默默伸展,花蕾羞答答在叶子里静静地开放,无声无息迎接着楼宇间透过的一缕缕阳光,用娇嫩婀娜的身姿和诱人的芳菲向从她身边走过的人送上无尽的问候和祝福。让人们感受到喧嚣之中的静谧,繁缛之后的简约。这,抑或是她们在“芸芸众花”中成为单位美女们最爱的理由,无论年少、资深,路过时总是心狠手辣地摘几朵,鼠标旁、包包中、发鬓间乃至轿车里,时常会有白兰花相伴。只是从来无须得到我的“恩准”,更有甚者,一些男士也陆续成了“采花大盗”,美其名曰,为了减消身上的烟油子味。我能收获的只是偶尔几句,你养的白兰真漂亮,你咋这么会养花之类不咸不淡的口头褒奖而已。其实每当这些时候,在我心中会荡起成就、满足的涟漪。给予身边的人美丽、芳香不也是一种德行吗,要么咋有“手留余香”之说呢?
有时候静默是无奈的抗争,是内心的呐喊;有时候静默则是修身养性,是成熟的孕育。
父亲在我成人后曾训斥我:“你要是活在我那个年代,早就打你八次右派!”这大概是因为我秉性中有着太多的癫狂、叛逆、张扬,缺少像白兰花的静默、平和、儒雅;也许是我对生活的感悟太过肤浅,没有像白兰花那样几度春秋、几度风雨的沧桑历练。佛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世界在哪里,就在那一枝一叶上。白兰花里不但有孔子的为人之道、老子的处世之道、庄子的养性之道,而且还有《大学》的修身之道、《易经》的天地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