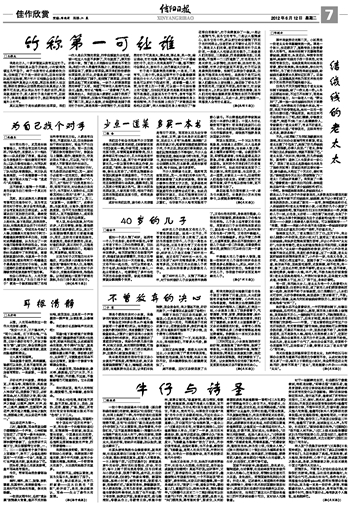□焦 杏
我们这个社会的机体不少方面都表现出或轻或重的病症,《病恹恹的图书馆》就是一例。作者写道,在他家乡的图书馆,尽管阅览室崭新铮亮,但上座率却只有10%左右,且大半还是老年读者,其次是儿童,至于壮年读者则寥寥无几。一位以前的学生遇见作者,如此说道,“老师,你也在这边看书啊,哎哟,你也太用功了。”经常见到媒体公布国民阅读率的调查报告,干巴巴的数据难以记住,但作者在文章中描写的这些情景却生动具体,提醒我们,国人其实少有阅读之风气。据日本回来的朋友说,人家的图书馆,相当于我们这里的街道或区县图书馆,经常是座无虚席的。
或许在我们这里,读书给人的联想是等同于用功,而用功又仅为应付学业、考试、文凭,读书本身并无乐趣可言,因此古人才有“头悬梁、锥刺股”之类的苦读之计。笔者曾因癌症晚期而动手术,手术之后,朋友或同事来探访,当他们见到我依然手不释卷时,不少人会惊讶地说道,你还在读书呀?我答,不读书,莫非在家等死?对方立刻说,你可以去公园晒太阳、打太极拳,或是在家看电视,唱卡拉OK,读书多累呀。
不少人觉得读书太累,确实有其客观原因。其一,在我们的学生时代,硬是被灌输了太多应试读物,语言课少教学生欣赏文字之美,更多却是死抠阅读理解题,寻求所谓正确答案,甚至就连写作文都有公式可套。如此启蒙而识字读文,怎么可能培育出对文字的热爱呢?其二,谋生之艰辛,应酬之繁忙,也导致不少人难有闲暇用于静心读书。不由得想起经济学家陈志武的一本著作之题目: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看来我们是该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们长时期以来忙得连读书的空暇都没有,却依然不能跻身发达国家之行列?
再说主观原因。一个习以为常的现象是,在饭桌上点菜时,主人总是多多益善,盛情款待。当曲终人散之际,桌上剩菜足够再吃一顿。公款招待不说,即便私款请客,也难见盆碟见底之景象。好客、慷慨本是美德,但浪费却是恶俗。更何况今天我们早已告别食物匮乏年代,如此的好客更是面子工程之陋习。我常这样想、也这样说,少点一道菜,足够买上一本书。但却常听人们抱怨书价太贵;即便三室两厅的豪华居室,似乎也难以容纳书架,更不用说布置书房了。
最后还想为出版社献上一计:请为书本瘦身吧,尽量多出小开本的袖珍书,以便随身携带阅读。
(据《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