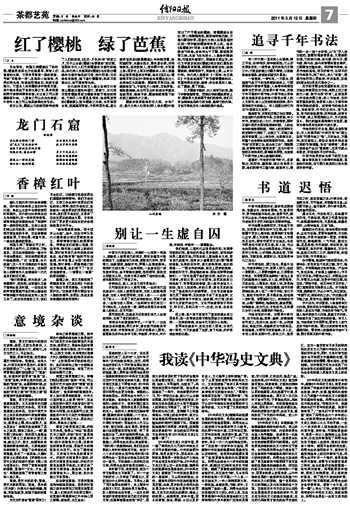□李松海
意境,是文艺理论中的常识式词语。然而,正因为是常识,人们又常常容易淡化它,忽略它。为文为艺之人,不应如此。
意境,是美学范畴,其范畴当属艺术辩证法。意境说,由来久矣。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中,在秦汉时期便提出了“心物”说,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则提出了“意象”说,在唐宋时期更有“缘境”说、“重意”说等。学界比较共论的、成熟的“意境”说,当属明清时期。近人王国维是“意境”说集大成者,他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则把意境学说推至巅峰。
意境,是文艺创作追求的至高至美境界。大凡在美学史闪耀着夺人光芒的艺术作品,无不是意境至上的作品,这在中国艺术史上在古典诗词和中国绘画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一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淋漓尽致地描摹了思乡之浓烈,惆怅之悠长。一幅“墨竹图”(郑板桥)简约而又浓厚地表现了雅士之风韵和仕宦之高洁。除此之外,散文、戏剧都注重意境的营造和陈设。大家熟悉的孙犁的散文,写就了白洋淀的风情意蕴,形成了一派风格。大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名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戏称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抒写了青春和爱情的颂歌,意境中“日光、月光、星光”等意象渲染了青春爱情之美和人性之真。
意境,是艺术的风骨;意境,是艺术家的灵动;意境,是作家(艺术家)内情与外物的相融;意境,是登临极顶、放眼万壑的快意和欣然。
为文为艺者当“意境”而求之!
结构之美是意境之要。美学理论中阐释的结构美大致是指艺术门类及艺术作品的营造艺术或技法。俗而言之,是指作品的布局与谋篇、章法与表述、技巧与语言等。以散文为例,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杨朔的《渔笛》都是在结构“术”上形散而神不散的典范之作。他们在结构上都十分娴熟地运用了艺术辩证法,实现了艺术的结构精巧之美。
诗意之美是意境之本。钟嵘《诗品》提出的“滋味”学说,可以说是对艺术创作追求“诗意”的直接要求。司空图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就是鲜活的意境追求。有人说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华文化某种意义上就是“诗学”,这足以表述着中国艺术或者说中国气派就是直追诗意的艺术,是诗的载体与写意。由此甚至可以说,意境就是中华文化在艺术领域的经典浓缩,是江南之水乡、是苏州之园林、是渔舟之晚唱……
语言之美是意境之魂。好的文艺作品,都是以“神似”彰显其艺术之瑰丽,好的“形式”就是语言(包括色彩、曲调、造型、材料等)的外在表现与力量。这里所说的语言是泛指,是指艺术的表现形式与技巧。但为了通俗起见,又常指文学作品的语言艺术。好的艺术语言是朴素的、好的艺术语言是单纯的、好的艺术语言甚至是平淡的。大家记住了语言大师老舍、侯宝林,大家更追捧着赵本山、周立波,其内在魅力不言而喻。
拉杂着说意境,不是把意境说到神秘诡异境地,而是把对意境之追求和赏玩之无限交诸君思忖,愿人们都在艺术欣赏过程中,在意境中寻得精神之升华和心灵之慰藉。诚如是,此文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