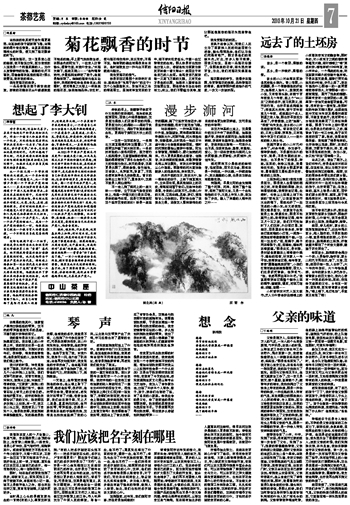□张德源
故乡,是一个美丽、温暖的词;
思乡,是一种美好、温馨的情。
故乡的小山村坐落在固始县武庙集乡境内。青山苍翠,小河潺潺,是一个清静雅致的好地方。如果前人如今人,既读武侠小说,又有经商头脑,在数千百年前或几十年前,起上个“××山庄”之类的名字,或习武聚义,或开店行商,也许早就名闻遐迩了;抑或风水流转,数千百年前或几十年前,忽然蹦出个名人、明星之类人物,那也许早该成为圣地了。非常遗憾,上述“如果”、“抑或”均未发生,故乡的小山村依然默默无闻。留在我记忆里的,只有土坯墙、茅草房,只有鸡鸭牛羊及它们的主人——我朴实的亲人和乡邻。
我离开家乡的小山村已40余年了。40余年里,作为游子,情牵梦绕的,不是漂泊在外的甘苦、荣辱,不是未酬的志向、抱负,也不是未了的情思、牵挂。说真的,你难以想象,我最难忘怀的,竟是故乡那星罗棋布、最普通而又最能显示贫穷、落后的土坯房。
土坯房何以难忘?我想大概是因为,那是我人生最初的栖身之所,有我最初的温暖、欢乐和最初的痛。我清楚地记得,生病时,母亲从土坯墙上刮下松软的“雨泡灰”,让我就着凉开水当药喝下,居然治好了一些无名的小病小灾。长大后我想,那大概是因为,农家孩子生来就是土命,健康成长,那是不能离开土的。我清楚地记得,每年正月十五之夜,我们不可能如时下人们这样,外出观灯展、放烟花,而是跟在母亲身后,举着油灯或纸糊的小灯笼,一间房一间房地将墙壁缝隙照个遍。一边照一边念叨:“照,照蝎子,蝎子死在墙裂子;照,照蜈蚣,蜈蚣死在墙窟窿。”那是仪式,是祈祷,是祈望免遭藏在土墙墙缝中蝎子、蜈蚣的毒害,祈求家人一年平安。我清楚地记得,每年春夏,常常“屋漏偏逢连阴雨”,小孩们忙着用破盆破碗接漏雨,而大人们总是阴沉着脸,唉声叹气:“唉,秋后再弄些草补补吧。”我甚至清楚地记得整个制作土坯的程序:割稻茬,碾压,用坯刀划线、切割,晾晒……
小时爱听农村艺人说大鼓书。艺人口中常会讲些绣楼上的小姐喜欢穷秀才的酸故事。那时年幼,对小姐秀才之间的暧昧情事毫无兴趣,却对绣楼之“楼”莫名向往:楼啥样呢?1960年夏,我小学毕业,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距家50里外的安徽叶集有楼。于是在某天凌晨,攥着打两天柴换来的4毛钱,步行上路了。我在叶集街中心那唯一的一座两层楼前停留很久,对着那唯一的一扇玻璃窗,展开了想象的翅膀:那里肯定有一位美丽的小姐,那里面一定如天堂般富丽堂皇。可惜,没有进去一探究竟。我那时实际年龄不满13周岁,当猛然想起半天粒米未进及漫漫50里回程,不禁直冒虚汗。我用两毛七分钱在商店里买了三角板和量角器,那是下半年上初中要用的,也是我此行的借口,之后,攥着余下的一毛三分钱,终于在天黑前赶回了家。事后,我居然觉得很值:我知道了楼是啥样的。也许你难以想象,那时,在我们那里,方圆若干里内,砖、瓦、楼都不是现实的东西,作为小孩,你只能“听说”而难得一见。
当兵之后,我去了南方。上世纪60年代,穷是各地农村的主题。但说实话,我认为南方农村譬如我所到过的赣南、闽西,农民的居住条件要比我们家乡强。土坯墙也有,但相对较少。赣南、闽西农村中一些用木板作墙壁的房子,也许简陋了些,但房上盖的,基本上都是小黑瓦,而非我们家乡的茅草、稻草。至于福建沿海农村,墙大抵都是石料,这当然是因为土坯无法与台风相抗衡。
谁不夸自己家乡好。我在战友面前吹嘘家乡这般好、那般好的时候,心中暗忖,我不会提及家乡的土坯房,我得遮着、掩着。
然而,曾几何时,家乡的土坯房竟踪迹难觅了。近些年偶尔回乡,闯入眼帘的,不是别致的小楼,就是精致的别墅。心目中的故乡,脑海里的土坯房,好像被魔术师玩了个时空大挪移,隐逸于历史深处了。
每回故乡,脑海里常会涌出一个词:人是物非。物非者,家乡山河已不再依旧。变了,大变,巨变。然而仔细一想,人也非了。六十年流年俯仰,六十年物换星移,当年的家乡老人多已作古。看着家乡的巨大变化,我内心常有一种莫名的冲动。真的,很想给天堂里的父母、乡邻发一封信:回来呀,回来看看家乡的楼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早就真正实现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