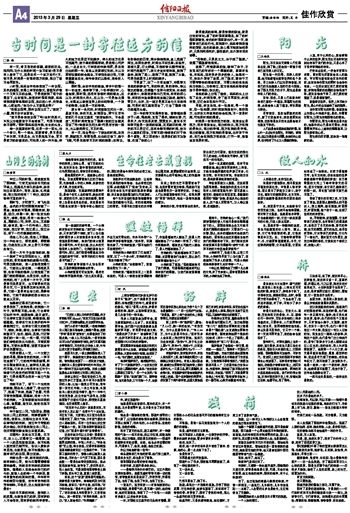□雪小禅
你,看过残荷吗?
如果是深秋或者初冬。寒冷的风中,有一片残荷,几乎是枝零叶败,几乎是失去了所有取悦的颜色。
完全是一副惨落的表情。那荷叶凋零的七零八落了,以枯萎的姿势倒在池塘里。那莲蓬也不那么饱满了,怕冷似的,小小的骨朵。依然的骄傲,依然的桀骜。
没有了夏天的热烈,荷正盛开时,有一种凌驾的气势——但不自知。自以为低调,却跋扈到清凉。自以为薄凉,却还是烈的艳的——那盛开的荷着实有些炫耀,当然,她也必有炫耀的资本。可是看久了,会厌,会腻,会生出反感。
你以为她会骄傲一世吗?
每朵荷都自己未知的前程。她们努力盛开,虽是自身光芒,却也是为了索取。
索取那眼前必要的夸奖和虚荣。
你看你看,这荷开得多妖多灿。
——是掩饰不住灼灼锋芒的。太过外露的东西消逝得快。荷最茂盛时带着不顾一切的表情,看着羞涩其实是疯狂了。开呀开呀,开得没了边,也没了际,也没了未来,也没了过去。
一意孤行,孤芳自赏——有谁知道莲的心事?说到底,莲是霸气的,是不顾一切的。她的完美,她的无意跋扈,都埋下了一个伏笔——当初有多盛大,以后会有多低迷。
一向,对那些太过盛开的花朵持有警惕,而对那些小小的花朵或者不开花的植物持有过分的喜欢。
不张扬,是做一朵花或者说做为一个人的最好的姿势。
但是,盛开的莲花太肆意。
她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一位群芳妒的开着。要多妖娆有多妖娆,要多华丽有多华丽。
然后,秋来了。
然后,她一步步的在冷风中受伤了凄冷、伤害,她的心,是一点点凉下去了。
先是形变了。
不再是盛大的开放模样。
那荷叶小了很多,那莲蓬不再圆鼓鼓了,呈现了一种枯萎的样子。
又一场冷风。
又一场苦雨。
……
已经不是秋了。到了冬。
残荷,呈现出一片残落的鬼魅。历经了那些风霜、打击和伤害,她看似寥落了,其实却有了铮铮的骨。有骨骼了。那有了骨骼的神经,远比一朵盛开的莲花更有味道。
她盛开时,只是妖媚和跋扈,她枯萎时,才真正有了风骨和气象。
残荷,以一种不让人怜悯却让人心生敬意的姿态出现在画家笔下。
如果一个画家只会画盛开的荷,而不是能画残荷,那只能是一个心灵地貌还不丰满的画家。或者说,他的审美还没有到凋零的状态,而人生的时光,还太耀太丰满。那样的人生,也是寡味的。
就像这朵曾经不忧亦不惧的莲,假如她没有受过冷雨凄风,假如她还是一直粉艳艳的盛开的,纯洁而无知的开着,她只是宫廷画中那无趣而带着稚气的一朵傻荷。
现在,她老了,她枯了。
味道和气象却出来了。
年轻时,只顾着一味地盛开盛开。那饱满的大荷花呀,看着是纯洁是壮丽,可是,不会对她有敬畏,她太单纯的纯粹。那样的纯粹,有什么味道呢?
老了,生出孤独的美感与凄清的味道。守着一杯清茶,一盏孤灯,几本闲书,几本书法孤贴……足够了。人生要的太多也是缺失,太过完美也了无趣味。
那稍显残缺的人生便是这冬日雪天的残荷。
一个人独钓寒江。
这山河是她的山河。
这岁月亦是她的岁月。
这酒言欢,可以醉,可以不醉——陶罐中是采来的残荷与枯萎的莲蓬,暗淡的灯光下,老条屏上有飞鸟、莲花、腊梅……散发出紫檀木特有的暗香。
把自己活成一朵残荷,不为懂得,只为慈悲。
当人生远离了那些浮华喧嚣热烈。远离了人群的热闹、名利、趋炎附势,人生,是往回收的。
收的姿势当然不会如盛开一样的夺目。
甚至,无人在意。
可是,荷,抽筋扒骨了。没有了灼灼夺人之姿,却有了硕硕风骨之态。
那《锁麟囊》中落了难的富家女薛湘灵怎么唱:他教我收余恨,铭娇嗔,且自新,改性情,休恋逝水,早悟兰因……
翻看杨绛、张爱玲、杜拉斯、陆小曼晚年的照片……这一朵朵残荷,有了隐忍却更为让人心动的风骨,那是光阴赠予她们的味道——历经岁月摧残,饱经了人世的风霜,脸上的光芒,却更加灼灼。
有友为我画荷。
我只要残荷。
那盛开凌厉的强势之莲花,不属于我。
那有了风骨的荷或事物,才是我的——它们在时间并不光滑的隧道里与我一一相认,我看着它们,它们看着我,找到最本质的共同属性:清醒自知、坚韧饱满、铮铮傲骨、自在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