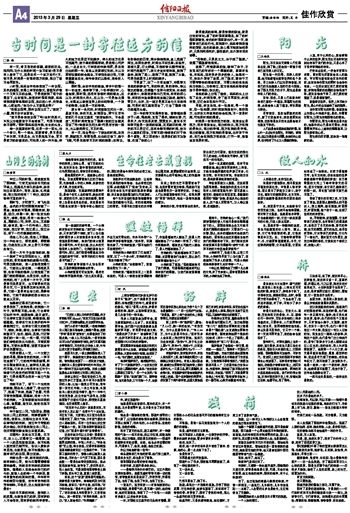□潘国本
是在流水与大地顶牛、赌气的时候,或者在山险水急、山和水互不买账的时候,桥就来了。桥将身子趴下,手搭牢这边,脚踏实那边,此时,争强两方便不由得笑了,气也全消了。世间总有磕碰,有了桥,不知少了多少疙疙瘩瘩。
桥是大地的良心,无论大小、高矮,无论构筑它的是铁、木、石、塑等任何一种材料,无论多险峻的山和多湍急的水,只要桥在,人们就再难看到山穷水尽,就再难遇到穷途末路。桥从来是不思考的,它只守一个理:有一天我不再背负了,我的生命也就没有了。
童年时代,村西长脚沟上也有一座桥,说它是桥,其实也只是三块长长的条石,架在五六米高的堍上,它那样粗陋、那样憨厚和不加修饰、不讲技巧,使龙冈上流过来的那股不讲理的泄水心悦诚服了。石桥没有受到任何惊扰,仍然朝夕匍匐在桥墩上,龙冈来水在桥下欢欢喜喜地淌着,两岸的草木悠悠然然地枯荣。我们村的男女进城,对岸村落的孩子来上学,安稳地踏过石桥,如履平地,没了艰辛。
三块条石,成了桥,就这样尽心,这样亲民,就这样日复一日,直至坍塌。坍塌以后,代之以堤,到后来农村格田成方,小石桥连影子也没有了。此后,没有谁再记起它、提到它。要知道,它一直连名字也没有。
生而为桥,就是驮人驮货的,就是以身铺路或者展示风景的。
这让我想起我的祖母,想起我们村的那些前辈。在世的时候,他们终年一身灰黑布衫,像桥;终日田头重担在肩,像桥。他们往往没个正规名字,只有诸如小狗子,大眼睛,姚老四,老来子一类代号。他们一辈子没做过一件大事,没说过一句让人记牢的话,没发生过一则动人的故事。来到这个世界,他们是专门出力和流汗的,是专门趴着身子让后人顺顺当当过山过水的。我的祖母,男人24岁眼睛就瞎了,她驮着一个八口之家,每天最早起来做最脏、最累、最琐碎的事,还总是吃已馊了的剩饭。后来她年纪大了,驮不动家了,改去驮孙子。她是一座桥,一座一个家的桥。到后来,她病得直不起腰了,没法子驮了,这年她也静静地走了。
一匹马生来是跑的,一座桥生来是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