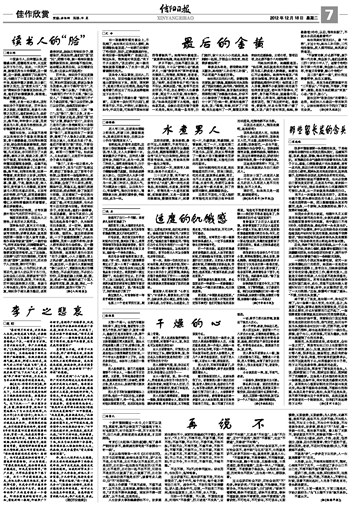□薛仁明
中国读书人,自宋儒以来,道德感太深,道德范围太窄,又过度以天下为己任。因此,一天天严肃,脸部肌肉也日益僵硬。这一僵硬,这一紧绷,遂绷坏了民族的气运,也绷出了中国文明之衰微。百年来,延续宋儒之紧绷,加上救亡图存之压力,这“重责大任”,“压迫”得知识分子脸部更加扭曲。于是,他们开始慷慨激昂,渐渐地,转成了愤懑乖戾。
性情,才是一切之根本。说句知识分子不爱听的话,百年来生灵之涂炭,关键原因,是读书人性情之失其正。他们始终以为,政府之根本问题,是制度法治尚未建立。殊不知,种种昔日之恶,其实是因为人坏,是因为性情扭曲,并非制度有多么的不足。
制度与法治,从来就不是清末以来知识分子想象的那般重要。昔日秦朝暴虐,但刘邦在建国之初,却全然沿袭嬴秦制度,照样开出了两汉盛世。而后,唐沿隋制,几无更动,亦同样开出了大唐盛景。秦汉之异,隋唐之别,都不在于制度,而在性情。论起性情,宋儒因道德观念狭隘,总瞧不起刘邦;觉得他既没读书,又像个无赖。殊不知,刘邦的性情,比那一帮儒者,实实要好上许多。刘邦凡事看得开,最有中国人该有的宽、厚、通、豁,于是,豁然大度,知人善任,没有读书人的酸腐,更没有读书人常犯的意必固我。正因有此好性情、好气度,故而连秦朝的暴虐,都伤害不了他;反倒那群满嘴仁义却性情褊狭的所谓儒者,最后多被踏杀。
有刘邦的好性情,才有汉朝质朴而大气的四百年好江山。
制度固然重要,但后头人之情性,才是历史之真消息。
国学热也好,复兴文化也罢,最要紧的,无非是要恢复中国人该有的性情;讲得更具体,就是要找回那一张张中国人该有的脸。现今某些专家谈“国学”,一脸市侩气;另有某些专家,则满嘴酸腐气。凡此恶气,不听还罢,一听,恐怕脸部都更要变形难看。见了这些脸,只觉得“五四”的打倒传统,可真有理!谈“国学”,谈传统文化,若无益于人之性情,那宁可不要!
自古以来,士为四民之首;直至近代,读书人仍以天下为己任,以社会良心自居,原都该有“君子之德风”的自觉。然而,不幸的是,百年来民族性情之丕变,是读书人带头迷失;而今,民族性情之恢复,知识分子却又最为殿后,甚至最持异议。独独只有知识分子,愤懑依旧,乖戾如常。他们忧“国”忧“民”,闭锁书堆,被一堆知识概念搅得脸面扭曲,却丝毫不能自知,还动辄以真理自居,以引领者自任。唉!这该从何说起呢?
百年来,知识分子因过度操切,以至于忘掉了:再怎么天下己任,再如何国家民族,都该以修身为其根本。昔日子路问“君子”,孔子答曰,“修己以敬。”子路追问,“如斯而已乎?”孔子又答,“修己以安人。”子路续问,“如斯而已乎?”孔子最后回答,“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是的,三次回答,三次“修己”;这“修己”,修己之身,才是一切天下国家之起点。要忧“国”忧“民”之前,都该先“忧己”,反省自己是否已然一身清爽而又一身明白?但是,近代知识分子不仅忘了要“修己”,甚至还找来了一套说辞,撇清了个人修身之必要。知识理论之误人,也莫此为甚!于是,他们不断援引“新”理论,不断论述“新”学说,整天痛骂,成日愤戾,终至一己憔悴干枯。如此误人,又如此误己,正是百年来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
“修己”,才是一切之根本。今日知识分子,因为“五四”包袱过深,都忘了要修身,忘了要有个好性情。以前遇有一些聪明学生,某段时日,突然性情大变,迷失得彻底;那脸,全变了个人似的。然而,隔些年后,再逢又见,他却已然迷途而后返;经此转折,除了恢复旧日样貌,反更增添了一份安然与淡定。于是,这曾经的迷失,反倒成就了他;无有这段波折,也未必有日后的沉静与安稳。我看知识分子,亦复如是。他们一脸躁郁,我虽说感慨,却也不甚忧心。因为,说不定,哪天因缘具足了,可能只是起身照个镜子,久未细看的自身脸庞,才一定神,赫然发现,果然不对,真真不对;于是,眼前无路,想回头,就这样迷途知返,一下子就幡然猛醒了。如此生命翻转,其实一点都不奇特;许多人都有类似的生命经验。这一翻转,于是,他们重新要修身,重新观照性情,还发现孔老先生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虽是老话,但还真有道理。就这样,一旦读书人重新知道“修己以安人”,重新担当真正引领的角色,不必成天议论,不必忧心忡忡,只要他们脸上的躁、怒、愤、戾,经此一转,渐渐化成了中国人最该有的宽、厚、通、豁,那么,一个真正的盛世,就指日可待了!
(据《人间随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