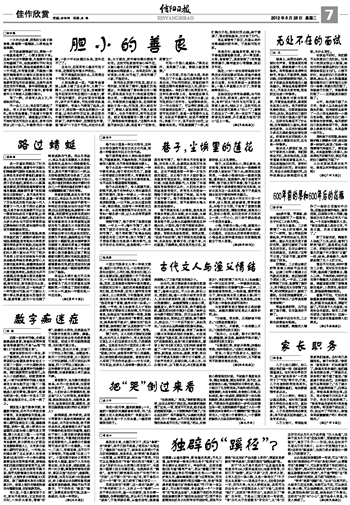□包光潜
中国古代很多文人有一种渔父情结,他们一边声色犬马,一边寻求安宁,身在庙堂时,心向江湖;而身在江湖,心却又念着庙堂。他们需要一个干净的地方、一个脱离世俗苦海的地方,安顿灵魂。其实,这是物质与精神平衡的需求。在烦扰的尘世中,他们的灵魂最愿意走向江湖,走向林莽,走向人迹罕至的青山绿水,上山砍砍柴,下河撒撒网,即所谓的渔父生活,恰如李煜《渔父》所言:“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纶,世上如侬有几人?”而如此赋有渔父情结的古典诗词,几乎比比皆是,如高适的“曲岸深潭一钓叟,驻眼看钩不离手”、张志和的“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柳宗元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以及陆游的“一竿风月,一蓑烟雨,家在钓台西住”,等等。
到了元代,文人的渔父情结更加强烈。在元代文人的画作中,有大量的《渔父图》,文人们追求渔父生活,已经蔚然成风。这是因为元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文人有一种“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心理感受,加上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致使许多文人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许多文人虽寻得一隅安身,心灵却陷入了万劫不复的苦闷之中。
在元代,渔父情结最为浓郁的要算与王蒙、黄公望、倪瓒并称元四家的吴镇了。他终生庶民,不入仕途;游乐山水,流连江湖。他一生很少结交达官贵人,往来的多是和尚、道士和隐逸文人。生活潦倒时,吴镇便到街上卖卖小菜,勉强度日,绝不谋取官职,绝不媚俗卖画。董其昌在《容台集》中记载:“吴仲圭本与盛子昭比门而居,四方以金帛求子昭画者甚众,而仲圭之门阒然,妻子顾笑之。仲圭曰:‘二十年后不复尔’,果如其言。”由此足以见得吴镇的孤傲与虔诚。
近来,我连续阅读、欣赏了吴镇的三幅主旨和图式相近的绘画。无论是“双雁齐飞掠水面,渔父仰首看斜阳”的《芦花寒雁图》,还是“渔父凝视聚思,愿者上钩”的《渔父图》,它们均给读者传递了一种“生在红尘、洁身于梦”的超然情怀。画寓意,诗言志。读着,赏着,我自己似乎便成为图画中那个右手摇桨、左手执竿的渔父,忘却尘埃,心系山水,与白鹭为伴,以飞霞为友。在《洞庭渔隐图》中,我们看到了元代文人(如吴镇)的一种玉洁的坚守、一种傲然的孤独、一种择壤而生的磅礴气势——近岸,三棵松树造型特别,一松旁逸,横贯两松主干,却在迷离水面上蓬勃上扬;另二松直拔而上,不倚不歪,负重昂然。这难道不是一种象征或者写照吗?
与许多赋有渔父情结的古典诗歌相比,吴镇的题画诗更是让人感觉非常。如:
“兰棹稳,草衣轻,只钓鲈鱼不钓名。”(《洞庭渔隐图》)
“山突兀,月婵娟,一曲渔歌山月边。”(临荆浩《渔父图》)
“孤舟小,去无涯,哪个汀洲不是家;酒瓶倒,岸花悬,抛却渔竿和月眠。”(临荆浩《渔父图》)
“云影连江浒,渔家并翠微。沙鸥如有约,相伴钓船归。”(《秋江渔隐图》)
看来,中国古代很多文人,他们在追求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同时,又不断地向不胜寒的高处进发。
(据《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