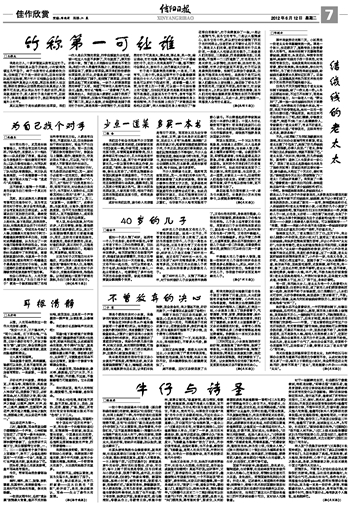□邱剑云
那年我家乔迁的第二天,小区里的一位老太太令我眼睛突然一亮。那是一个秋日,桂花都开了,宽路窄径上弥散着怡人的香气,她坐在桂树下的藤椅里结着绒线,瘦瘦的,头发花白,神情专注而慈祥。她握针勾线的手指十分灵活,对我特别有吸引力。当她发现我站在她身边看着,便对我笑笑。我也笑笑。学生时代学琴时,为了使手指灵活我结过绒线,结绒线的感受便永久留在记忆里了。近些年来,这项颇具技术性乃至艺术性的传统手艺在里弄坊间越来越少见。
但我几乎天天能看到这个老太太坐在树下结绒线,结了一件又是一件。入冬之后都还在结,不过已不在树下,而是坐到朝阳的地方,与一些老人一起“孵太阳”了。那一抽一动的绒线在阳光下显得特醒目,也衬得她的手指格外灵动。有一回,我忍不住夸赞起来。坐在一边的一位老先生接口道:“那还用说,她的这双巧手还传给女儿了呢。松江顾绣,非物质文化遗产,知道不?她二女儿是顾绣传人,专家级的!”老太太听了,有点不好意思,反驳老先生道:“看你说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瞎联系嘛!”
不久,小区里贴了为灾区捐款献衣的通知。我正在办公室询问有关事项,看见老太太提了个包来了。她捐了好几件绒线衣,又要捐款,办事人员说:“丁老太,你每年捐出这么多绒线衣,钱就不要捐了吧。”老太太说:“衣归衣,钱归钱,打几件绒线衫,算啥呀!退休工人也要多尽一份心呀。”原来丁老太这么起劲地织毛衣是为了捐给灾区啊!回家后我把这事对妻一说,妻也感动。大约过了十天左右,妻对我说:“你知道我今天去买小菜碰到谁了?丁老太!已经88岁高龄了。我俩谈了一路呢。”接着便是一连串的自问自答:你知道她这些年来一共捐了多少绒线衫吗?四五十件呢。你知道她哪来那么多绒线的么?都是从儿子女儿孙子外孙家拿来的,大多数是压在箱底的新绒线,还有半新不旧的绒线衣、绒线裤,她不让小辈们丢了,拿来拆拆洗洗,又结成了新的……还有,你知道她还给什么人送绒线衫吗?老太太特喜欢小孩,小区里好几个小孩穿了她送的绒线衫呢,前天还给打扫卫生的阿姨送去一件。阿姨给儿子一试,正合身,又好看……我打断了她的话,也来了个设问:“你以为那个阿姨就因为这个才感谢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小孩穿上高龄老人做的衣服,可以添福添寿……”“我懂,我懂——我家小外孙是不是也要她一件绒线衫穿穿呀?”“这怎么好意思开口呢?”“是呀,不好意思的。”
谁知没过几天,丁老太倒自己开了口。这天下午,我去幼儿园接小外孙回来,走进小区大门,就看见丁老太坐在墙边结绒线。我快步走到她面前打招呼,并让小外孙叫“太太好”。也许是有缘吧,老太太把他拉到身边问长问短,又摸着他的头问:“太太结一件绒线衫给你穿,好吗?”小外孙有点害羞不知怎么回答,我连忙表示谢意。过了一星期,老太太就把绒线衫送到我家里来了。小外孙一穿,也是又合身,又好看。我们心里过意不去,就随手拿了一大块火腿聊表心意,她坚决不收,说她爱吃蔬菜,尤爱辣椒,却不吃肉。我一听,急了,这怎么行呀,营养不够呀。老太太一笑,说不碍事,她饭吃得多,每顿一大碗,半斤。啊,不禁为她的好饭量惊叹!老太太说她是湖南人,年轻时在家务农,后来随丈夫到此地,在铁路上干过,在工厂里干过,身体好着呢。
有一回,我问她大女儿:老太太为啥一个人住着呢?大女儿遗憾地说:自老伴去世后,成了家的儿女们都要接她回家一起住,她坚持不给子女添麻烦,自己照顾自己。儿女们无可奈何,只好争着给她钱,她说退休工资足够用了,不要。他们细心观察,见她为灾区结绒线结得很开心,便开始不断给她准备“材料”了。
她好像永远不会累着似的,一年四季都在树下、在墙边结着绒线。乐呵呵的,很舒心。然而,那天我上班的路上碰到她,发觉她很不开心,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问她到哪里去,说去办点事,便匆匆走了。后来才知道,她是去旧房拆迁的管理部门交涉呢——一年前,丁老太曾经住过并有过户口的旧居拆迁,有关管理部门曾告知她,按政策她可以得到部分拆迁款,可最近不知怎么一弄,说拆迁款不给了。她觉得没道理,这不是欺负人嘛。湖南人的烈性便上来了,定要讨个说法。那办公室里的人说不出个所以然,却坚持不给钱。如此几次,老太太终于生气了,坐在办公室不走,非要听个合理解释不可。后来惊动了上级,事情才又以丁老太的“舒心”而告终。
我无法想象这样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如何单枪匹马在那办公室里为遭遇不公据理力争锲而不舍,从此对她的敬重又多了一层。每天上下班经过小区时,我会常常走近去向她问好,称呼不再是“丁老太”,而是随着小外孙——叫她“太太”。(据《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