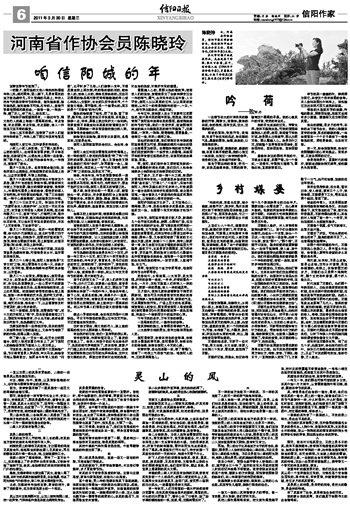一
一直以为灵山的风是有灵性的,山里的一切都是风从远处搬运来的。
村庄、柳树、牯牛、黄狗,以及面容模糊的村人,似乎都与那窜来窜去的风有关。
因为,我曾亲眼目睹了一股风搬走一座巨大的草垛的全部过程。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去上学,走在山垭口,突然起风了。那风是墨绿色的,披着长发,踮着一只脚,风风火火的过来了,还带来一阵瓢泼大雨。走到我身边,她犹豫了一下,可能是看我太弱小了,没有带走我,却把谁家堆在山腰的草垛衔走了。
灵山森林茂密,山谷幽深,给山风提供了施展野性和才能的空间。尤其在夏天,经常听到风把一头猪一只羊一棵树搬来搬去的故事。
山里人对风都有敬畏之情。
二
风是山里的精灵。
有风的地方花儿开的艳,草儿长的绿。有风的地方就有炊烟有鸟鸣有狗叫有人声。
刚插进泥土的柳枝见风就活,才出蛋壳的鸡崽见风就会叫,呱呱落地的新生婴儿见风就长。再丑的婆娘在风中理一理头发,嗨,立刻就漂亮三分。
我家小院种了棵香椿树,两年了一直不长个儿,在其根部上了许多肥料也没有效果。父亲抬手摇了摇树干说,缺风。他指挥我们姐妹把树移栽到门外的池塘边。
果然,这棵香椿在水塘边得了风水,就像人得了机遇,在时令的风里东摇摇西晃晃,左右逢源,呼足了阳光和空气中的养分,第二年,就长得枝繁叶茂。
此后,这棵树年年抽枝发芽,醇香的枝叶,香醉了我的童年,成为我留恋家乡的一个标志。
三
风从这村庄跳到那村庄,从这山坡转到那山坡,把一些声音、气味和各种信息在彼此间传来传去。
风是最灵通的使者。
我家的牛和邻居表叔家的牛一直要好。放牧时,俩牛如影随行,很好管理,两家因为牛的关系也相处的很和睦。有一天,表叔为了给孩子凑够学费,决定把牛卖给一外地人。
那天,当牛贩子把表叔的牛装进一辆破卡车扬长而去时,我的牛突然挣断缰绳,拼命朝车的方向追去。足足追了五里路。我和表叔家的二妹也跟着足足追了五里路。跑累了,我们就停下来心疼地抚摸着也跑累了的牛,想来思去,大哭了一场。
第二天清晨,奇迹发生了。我们发现表叔的牛居然和我的牛亲密地卧在一起,浑身还冒着热腾腾的蒸气呢。
表叔背着手绕着牛琢磨了一圈,最后伸出一根食指很有见地的说,都是风惹的祸啊。
风把牛粪的气味吹得老远老远,牛就寻顺着熟悉的味道找回了家。
四
灵山的风是热情的,就象一场又一场戏的伴奏,不停地敲打着鼓点。
在风的鼓动下,田野替换着颜色,村庄变幻着摸样,岁月更改着节拍。
有风的日子常常是恋爱的时刻。庄稼与庄稼恋爱,家畜与家畜恋爱,姑娘与小伙恋爱。
某个傍晚,灵山冲的荷塘在微风下荡起涟漪,谁家姑娘出落得如一枝新莲在池塘边浣衣。忽然,树林里传来一阵熟悉的芦笛声,姑娘羞涩的拽着被风吹动的衣襟,一袭嫩绿的碎花小褂,怎么也藏也藏不住一颗青春的滚烫的心。在风的感召下,姑娘勇敢地走向爱情。
在小伙多情的芦笛声里,夜色渐渐的深了。
夜幕降临的晚风,足足的是位热心快肠的媒婆呢。
五
无数文人墨客都企图解读风。
树欲静而风不止;山雨欲来风满楼;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长风破浪会有时。等等。
然而,对风感悟的最深,利用的最好的,还是那些可敬的乡亲。
他们一生与泥作伴,与风共舞,土地在他们手里如一团绵软的泥,变戏法似的,捏条渠是渠,搓条路是路,种瓜就能得瓜,种豆就能得豆。他们把握着风,改变着风。风也把握着他,改变着他。
给儿女盖新房、为老人选寿地要请阴阳先生看风水。春天里撒种子,秋天里扬稻谷,村人都爱在田埂上插一支系着布条的木棍,为的是辨别风向。好苗子的树和蔬菜,要种在阳光充足的高处,是为了得风。清晨起来打开木板门,伸手试探一下风就能安排好一天的活计,知道今天要干什么。
时下人们流行的词语诸如接风、借风、跟风、追风、捕风捉影、见风使舵等,大概都是从我的乡亲们那里借鉴来的。他们因时而作,顺应自然,是世界上最高明的风水大师。
有趣的是山里人对风还有独到的见解,常常用风来形容一个人的品行。爱图小便宜的叫占上风,乱搞男女关系的称风叉、败坏门风,爱买弄小聪明的为出风头,一夜暴富的是树大招风。
有一年秋天,人们不经意的一棵木籽树忽然窜出瓦屋脊,在秋风里招摇金黄色的旗帜,得意的很。村头的刘木匠瞄见了,朝手心吐了口唾沫,掂了掂手里的锯诡秘的一笑,说道,嗯,这棵树要成材了。
六
不一样的地方造就不一样的风,不一样的风造就了人的不一样的脾气性格和容貌。
山里人粗粗一看,好像没啥区别,但是,从他们站在风里的姿态,说话的语气,脸上的笑容,甚至从他们飘动的头发,深陷的眼窝,眼角的皱纹,手上被风吹的裂口,却能分辨出他是哪一座山凹里的人。
我们灵山的风和其他地方的风是不一样的,造就的灵山的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灵山的男子非常聪慧而又文雅,他们说话不象其他地方的男人没心眼似的扯个嗓子喊,而是带有磁性的很稳重地与人交谈。那是因为灵山的风是扩音器,能把声音传递的响亮高远,天长日久,灵山人说话就既简洁又明快,既省时又省力。
再如,灵山的女子比其他地方女子的牙齿白,脸蛋红,那是灵山人独有的石榴白山里红呃。不仅仅是因为山里的泉水清澈,不仅仅是因为山里的阳光明亮,实际上那也是灵山的风描绘的最美的花朵啊。
我在少年时,面颊也盛开着令人骄傲的山里红,离开家乡三十年了,城市的自来水早就把我那儿时的印记冲洗得不留痕迹。我常常驻足在城区的某个街巷,朝家乡的方向眺望,回想着我那美丽的姊妹们,在山林里穿行的俏丽的模样。
我感到家乡的风甜甜的,爽爽的,从我的心头生起。风还带来几滴雨,轻轻打湿我的忧伤。
七
一拨又一拨的山风弹奏着岁月的琴弦,像一首老歌,历久弥新,我们百听不厌。
风把山路吹得弯弯曲曲,把大道吹得宽阔平坦,把村庄的茅屋毫不留情地搬走,一栋栋小楼这些城市的复制品,忽然就又在风中昂然挺立。
风塑造在我们的生活,改变着我们的世界。
一年又一年,我们那些可亲可爱的家乡父老,在风中如一片片树叶,从青翠欲滴到叶落归根,然后,飘逝在季节的风里。
风,曾经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最后,他们也变成风的一部分,泥土的一部分。就像他们在二十四节气里耕种一样,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该忙时就忙,该闲时就闲。他们知道自己到了该歇下的年龄,就彻底的歇息下来,隐藏于一缕风或一撮泥中,把忙碌的事情,留给后人。
一茬茬的风吹老了一茬茬的人,不老的是山和水,是生生不息的风。
我仍然对风有敬畏之情,这种敬畏的情感包含更多的是怀念。人到中年,我喜欢听风声。尤其是在乡村的傍晚,我从一阵阵的风的语言里能听到乡邻的声音母亲的声音,那些远去的乡亲的声音。
八
那天,我在村口临风而立,正赶上是冬日的风。我并不感到寒冷。我看到不知疲倦的风窜来窜去,如我在童年时看到的一样。她辛勤地搬来铺天盖地的雪花,在天空挥洒。大地披上绵软的雪被,温润的泥土里,一些新的生命支楞着耳朵,聆听着风的呼唤。这些小生灵即将穿越泥土,携带着又一个春天的消息在萌发,萌发。
我童年时的感觉是对的,我们这些生命都是风从另一个世界搬运过来的,为完成某个使命搬运而来的。春华秋实,四季更替,伴随着梦想和希望,走过岁月的风风雨雨。
风是泥土的呼吸,是田野的招唤,是流水的歌声,是森林的呐喊。
有了风就有了生命,风是缔造生命的天使。
我的家乡我的风啊,我们感恩于你那伟大的生命奏鸣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