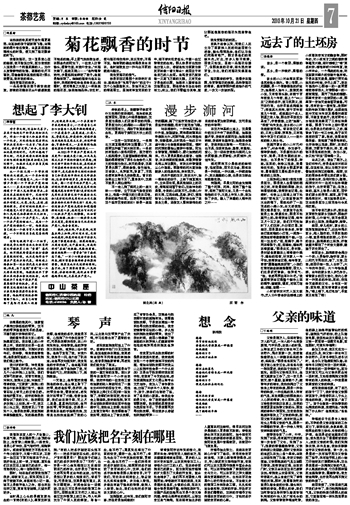□沈 凡
在清晨的微风中,谁家窗户里传出轻悠悠的琴声,这不绝的琴声激起我无尽的思绪,不禁引起对往事的回忆。
我的童年是在大别山的怀抱里度过的。我在镇上的小学里上学,我的班主任是一位名叫陈雨霖的老师。不到30岁的年纪,很和善,嘴角常挂着微笑。他是信阳城的人,独身来到我们镇上教书。
我10岁的时候,神使鬼差地走了邪路,不好好念书。我和几个小伙伴到山上去玩,我们用弹弓射麻雀,用青竹筒装上米和水,放到火上烧,米烧成了喷香的饭,“过家家”,跑到山的峡谷中抓住葛藤打秋千,躺在青石板上看天上的云卷云舒。谁知好景不长,逃学的事陈老师告诉了我的父母,陈老师还多次到山上找我。有一天,我正在山头上玩,远远看见山下走来个人,像是陈老师。我就到树林里躲藏起来。来的果然是陈老师,他喊我的名字,我就是不理,心想到了中午你总该走了吧。可是陈老师并没走,在山中转来转去,呼唤着我。他的声音很大很洪亮,喊声在山谷中回荡。他终于发现了我,向我扑来,我身子一闪,他扑空了趴在地。当他再次站起来时,我发现他的手掌流血了。他丝毫不顾伤痛追我,终于他抱住了我,凭着他的气力,把我拽到山下,拽到教室。
一天晚上,他特意把我领到他的住处。他从墙上取下了把琴,然后他拉琴,很好听,他把琴交给我,要我试试。后来我对拉琴有了兴趣,经常去他家,我们坐在院子里,天上月儿高悬,星星亮闪闪的,他开始拉琴,琴声悠扬,仿佛是一股清泉在他的手指间流淌,这清泉也渐渐地滋润了我的心田。从此我与这琴声产生了共鸣,学习成绩也有了显著的长进。
后来我就到信阳城上了中学。我曾在学校门口见过陈老师,他说他就住在南城,我真后悔当初咋不问清他的详细住址,或者是到他家看看。再后来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我想寻找他的原因是由于我的一篇文章的发表。我21岁那年在信阳市一个小学当老师,我把学校的一位老校工爱校如家的动人事迹写成了一篇长达4000字的报告文学,没想到竟在上海《文汇报》第一版发表了,老师们向我祝贺,校长在会上表扬我。我突然想到,若不是当初陈老师把我拉回学校继续学习,我能当上老师,能在报上发表文章吗?陈老师教会了我拉琴,我还当上了音乐老师,成了省音协会员,这完全与陈老师对我的熏陶有关。我要感谢陈老师,于是我在南城一带四处寻找陈老师的住处,我走进铺着青石板的小巷,多么想能听到陈老师的琴声,我找了很长时间,然而小巷里除了卖油郎的木梆声和人们搓麻将哗啦啦的响声再没听到其他声音。
使我更加怀念陈老师的时候是在我退休前后,我突然间发现一个令我吃惊和不安的问题,假如当初陈老师不把我从山上拉到学校会是一个什么状况?正是由于陈老师把我拉回学校,使我有了今天的生活。后来我调到地区文化局从事专业文艺创作,我加入了省作家协会,出版了30多本个人著作,妻子、孩子、弟妹们也都进了城,有了各自的小家庭。给我生命的是父母,给了我前途的是陈雨霖老师。陈老师的恩情我将永远报答不尽。于是我要再次寻找陈老师,寻找我多么希望能听到的琴声……